没有困难,创造困难也要上
读者,你好。
欢迎回到《吴军来信》第二季。
今天的这封信,和思维方式,以及认知有关,我们要讲一种思维模式,叫“没有困难,创造困难也要上”。
我们每一个人,做事情都希望自己遇到的困难越少越好。当然,很多时候,事情太容易了,做起来就不显本事,于是很多人就总想着解决一些难题,大问题,来彰显自己的本事。有的时候,如果问题本身不复杂,有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,他们会故意把问题搞得特别复杂,然后再把创造出来的复杂问题解决掉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没有困难,创造困难也要上”的思维。
还有一些人,不去解决实际问题,或者问题当中的关键,而是去发明一些原本没有的问题,把它们解决掉之后,自鸣得意地吹嘘。
有的同学不要觉得我说的这些情况是我编出来,在生活中这种人,这种事非常常见。比如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有一年撤销了一种治疗特殊忧郁症的处方药,原因是FDA发现,药厂所声称的那种疾病根本不存在。FDA讲,你不能为了卖一种药,去发明一种病。
当然,很多人做事不至于这么荒唐,但是却有一种“发明问题,再解决问题,没有困难,创造困难也要上”的思维方式。
“创造困难”的三个案例
我不妨给你看三个例子,其中前两个例子都是来自于我们同学的留言,而且很有代表性。
第一个例子来自第118封信讲“红眼睛,蓝眼睛”谜题的课后留言。一位同学讲,“老师,我感觉有一个逻辑漏洞,为什么(离开岛上的周期)要以天为单位呢?,不能以小时为单位吗?”这就是典型的“没有问题,要发明一个问题再来解决”的思维方式。当然,比较耐心的老师会花时间去解释,说题目就是这么设计的,没问题,或者有前提条件,离开岛上的船是一天一班,等等。但其实,这类延伸问题偏离了原本问题的关键,反而分散了目光,导致抓不住重点。
第二个例子是,每次我谈到“凡事要以事实为依据”,或者“事实总是对的”这件事的时候,总有人留言问,如何判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真的,如何证明眼见为实。我在《逻辑思维训练》课程中多次讲过,任何交流都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语境。
比如,司法部门经常说“以事实为依据”这句话,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,就是那些事实经过了核实,本身属实,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事情。讲这句话通常是要表达,不能以领导的意志为依据,或者以什么教条为依据。如果有人一定要问“眼见一定为实吗”,或者“如何确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真实的”,就已经跑题了。本来没有的问题,就被生生创造出来了。
第三个例子,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。什么是青苗法呢?在农村生活过的人,都知道青黄不接这件事,就是上一年收获的庄稼已经吃得差不多了,今年的庄稼还没有收获的那段时间,通常是暮春时节,三、四月份左右。这时一些贫困的,或者没有余粮的百姓,就需要一两个月的接济。等到了初夏,今年的庄稼收获了,欠债就能还上。
当然,放贷的人要追求利润,会收取利息。当时私人放贷的利率差异较大,有的比较高,于是王安石等人就想出了由官府放贷的做法。由于贷款的时候田地里的苗还是青的,因此称为“青苗法”。实际上,官府一年有两次放贷时间,春夏各一次。当然,官方标定的利率比民间要低。
这个做法看似很人性,也很合理,结果却是导致北宋末年很多农民破产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
当时民间借贷虽然标定的利率很高,但实际操作是按照市场行情来的,和官方规定的利率相比,并不算高,甚至更低。当时任山阴知县的陈舜俞在《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状》中讲,当时民间借贷,如果是信誉好的人借,月息不过1分半到两分,只有在少数借得比较急的情况下,才有很重的利息。
我把这段原文放在了文稿中:“民间出举财物,其以信好相结之人,月所取息不过一分半至二分,其间亦有乘人之危急,以邀一时之幸,虽取息至重,然犹不过一倍”。
而当时,官方借贷的利息是固定的两分,也就是说,有时候比民间还高。此外,民间的借贷周期有长有短,很多人不需要借很长时间,借个十几天,一个月,应下急的也有。而官方贷款不仅利率固定,贷款周期也是固定的,借短了不行,借长了没有。
很显然,民间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商业活动,本身不是问题。但是王安石却把不是问题的事情当作问题,然后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答案。当然,如果只是民间和官方公平竞争,大不了百姓不从官方借钱就罢了。但是各级官员为了政绩,强行摊派。王安石甚至在《周官新义》中说:“无问其欲否,概与之也,故谓之平”。意思是说,不要问老百姓需不需要,都要借给他们,这样才公平。对于官员,朝廷实行计息推赏,否则罢黜的考核制度。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,很多百姓甚至一些富户,逐渐走向了破产,百姓当然怨声载道。
为什么我把前两个例子和第三个看似略有差异的例子放在一起讲呢?因为它们都是先发明问题,再解决自己发明的问题的典型案例,有些持有前两种想法的人,一旦有了王安石这种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”的想法后,可能会不断发明出大问题,然后去彰显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人工智能领域的假问题
很多时候,世界上的问题并不复杂,我们只是想多了而已。比如今天关于人工智能危害的问题,在很大程度上就有点过度担忧。我这里举一个前段时间刚发生的例子。2025年2月,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全球人工智能行动峰会,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政要都参加了。这样的会,通常会发表一个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宣言,作为全世界的指导。
不过,这一次很多国家都没签署宣言,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原创性贡献最大的英国和美国。这里顺便说一句,著名的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,和获得诺贝尔奖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AlphaFold,都是由一家英国公司,也就是DeepMind主导开发的。那为什么很多国家不签呢?你如果打开那个宣言看看,就会发现,尽管它看起来很有全球指导意义,但实际上内容比较空洞,更多的是关注一些不那么核心的问题。
为什么说这份宣言有些空洞呢?里面一共六项主要内容:
第二项,讲这次峰会强调了加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多样性的重要性。
第三项,承认现有的人工智能多边倡议。
第四项,承认需要进行包容性的多利益相关方对话和政府合作。
第五项,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,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,需要以提高信任和安全建设为前提。
第六项,期待下一个里程碑。
虽然这些内容看起来有一定的普遍性,但在我看来,它们实际上没有有效聚焦和解决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核心问题。
比如,《宣言》开篇就讲,要“让AI为人类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服务”,并把它列为第一优先事项。这件事本来不是问题。有人可能会担心,将来人工智能会不会用掉很多电啊,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个问题,甚至有专家警告称,未来几年AI消耗的能源可能相当于一个小国家消耗的能源。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出来的问题。一个小国家通常是指人口1000万人左右的国家,以荷兰为例,耗电量占全世界的0.5%左右。还有人提出,如果AI持续高速发展,会达到沙特的用电量。沙特是世界上人均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之一,我看了它的用电量,排名世界第十,但只占世界的1.5%。
再比如,《宣言》里面还有一条承诺用“开放”、“包容”和“道德”的方式开发人工智能技术,这和美国近来反对的DEI,也就“多元、平等、包容”政策有一定相似之处。不可忽视的是,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技术参与的背景和需求有差异,不能简单地要求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,按照各国的人口比例来。
其实,今天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,是有了很多看似很有前途的技术,但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产业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革。现在最关键的,是找到一些能够马上收益的产业。
政客、政治家和企业家:谁在解决问题?
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,政客(politicians)是一个贬义词?因为他们在不断发明问题,而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,远不如发明问题的速度。
与之相对的是政治家(statesman),虽然有时这两个词会被混用,但在很多时候,它们一褒一贬,截然相反。政客指的是为了当选或获得权力不择手段的人,或者在政府部门任职、混事的平庸官员。而政治家则是为了所代表的人民的共同利益而竭尽全力的人,并且通常指那些有远见卓识,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人。
政治家通常受人尊敬,因为他们解决问题,而且能发现哪些所谓的问题,其实不是问题。而政客们常常会为了政绩,先把情况搞得很糟糕,然后再做点事情,让情况显得没那么糟糕。
如果说政治家是从宏观的角度解决大问题,那么企业家常常是从微观的角度解决具体的问题。因此在崇尚商业的社会里,企业家要比政客们受人尊敬得多。出于赚钱的考虑,没有哪个企业家会没事找事,专门给自己制造麻烦,他们通常都是能简单就简单,能直接就直接。
2025年3月份,美国一些退休的政府高官对马斯克发话,说你不能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理政府。但是支持马斯克做法的人说,正是这种思维误区,导致政府效率低下,美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,都是没事找事创造出来的事情。
虽然绝大部分人不会有政客的能量,能发明影响社会的大问题。但是发明问题,再解决自己所发明的问题的思维,很多人都有,它小到我在这封信一开头举的两个例子。这种思维一旦养成,以后在工作中就可能会不断发明问题,容易让自己陷入发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怪圈,然后自己可能觉得还挺有成就感。但是在外人看来,这种做法贡献为零,甚至是负的,因为浪费了资源。
我们做事情的目的,是要把世界上的问题变少,而不是变多。本来,随着世界的发展,就有很多新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,我们已经不容易了,还要发明不存在的问题,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了。
好,这封信我先和你分享到这里。下一封信,我们来谈谈科学思维的三个要点,我们下一封信再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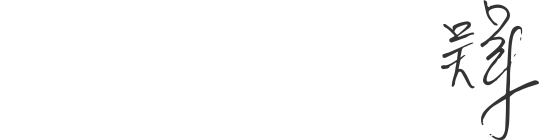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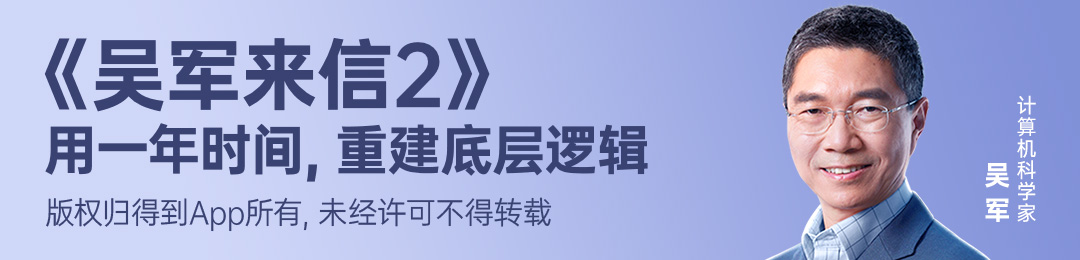







 浙公网安备 33010602011771号
浙公网安备 33010602011771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