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LIR:一场还没来得及成功的统一梦
“有些系统不是为今天设计的,而是为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预备的。
MLIR 是这样一个系统。 它想统一 AI 编译的碎片,却最终成了所有人都在用、没人能统一的工具。 不是它不够好,而是现实不允许它成功。
这是一个结构主义者造梦的故事,也是技术理想在产业逻辑中反复折叠的一次回声。
一、那年我们一起造框架
2018年,AI 世界像是一片野生雨林,繁茂、热闹,但也杂乱无章。
TensorFlow、PyTorch、JAX、ONNX、Glow、TVM、XLA、TFLite……几乎每一个新的 AI 项目背后,都在偷偷孵化自己的“编译器小怪兽”——不是重新发明中间表示(IR),就是造出一套别人看不懂的“图结构”,再配一套只在特定硬件上跑得动的 Pass 链。你要是没个自定义 op,连开会都不好意思举手发言。
每家都觉得自己做得最先进,最后拼成一幅奇观: 同一份模型,不同框架转换一次格式,不同芯片转换一次指令,不同团队还要“友情手动修图”,最终像在黑箱里扔飞镖,哪一步失败都不奇怪。
这不是技术进步,是“编译内卷”。
而在 Google 内部,情况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。TensorFlow 一边拉着 TPU 项目狂奔,另一边还要支撑 Android、Web、云平台等一堆周边工程。你以为它是一套编译器系统?错。它更像是一堆堆工程师“临时扔上去能跑”的脚手架。
Chris Lattner,当时还在 Google Brain,负责支持 TPUs 和好几个内部定制的 AI 加速芯片。他不是个普通码农,而是 LLVM 的奠基人,你用的 Clang、Swift 编译器,全是他一手打造的。从 Apple 出走再入 Google,一方面是继续做工具链,另一方面,他也嗅到了 AI 编译器世界的“内爆危机”。
有一次 Chris 跟 Jeff Dean(当时的 TensorFlow 负责人,也是 Google 大脑的“总工程师”)一对一聊项目方向,Chris 直接摊牌了:“我们正在重复造轮子,而且造得还不咋地。”
这话说得不重,但听得人心里拔凉。Jeff Dean 一向温和,但听到这话时,眉头皱了皱,像是终于有人说出了他自己也憋了很久的那句话。两人当时站在 Google Brain 三楼的阳台上,喝着黑咖啡,脚下是工程师们拼命敲代码的开放工位——“每一行都可能是在修补某个框架的编译 bug。”
Jeff 看着远处,淡淡地说了一句:
““我同意我们确实有个编译器问题。那你干脆去造一个新编译器,把这摊子统一了吧。”
Chris 后来回忆说,那一刻他心里其实挺复杂的——这不像一个项目立项,更像一个“祝你好运”的托孤。他既得到了授权,也背上了锅。
Jeff 给的是空间,而不是资源。他没有立刻拨人、派 budget,也没有拉 Core Infra 入伙。这是典型的 Google 式放权:你自己看着办,但做得好我罩你,做砸了你自己背。
Chris 没怂。他没像传统方式那样先写 proposal 去排期,而是干了一件 “LLVM人” 最擅长的事:
拉了几个能打的核心开发者,进了个白板会议室,直接三天三夜锁门画图。
这几个人,有的做过 ASIC 编译工具,有的是 TensorFlow Lite 的主力,有的是 LLVM 的资深贡献者,全是那种“白板战士”:一边画着图一边骂工程流程烂,一边动手写原型。
他们不追潮流,只关心一件事:
““有没有一种表示法,可以同时服务 PyTorch、TensorFlow、JAX,也能跨越 TPU、GPU、NPU,甚至是未来还没发明出来的加速器?”
听起来像是白日梦。但他们当真了。
房间里写满了 IR 结构、数据流图、优化 Pass 的依赖关系、前后端接口模型。Chris 提出一个关键设想:
““我们要一个多层次、多方言(dialect)、模块化的 IR 框架,能在同一套架构里处理从高层 DSL 到底层指令的转换。” “每个子系统都可以定制自己的小语言,但最终都能汇聚到一个统一的优化平台上。”
这个想法后来被称作——MLIR:Multi-Level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。
Chris 没有从 TensorFlow 出发去做兼容,也没有按 LLVM 的老思路去做统一,而是用了一个看似更复杂、实则更优雅的办法:允许复杂性自然存在,但让它们有秩序地共处。
他做的,不是“又一个编译器”,而是“一个造编译器的操作系统”。
那时没人知道,这个叫 MLIR 的玩意,几年后会撑起几乎整个 OpenXLA、Triton、甚至部分 CUDA 后端,也没人预料到,它会成为 LLVM 基金会接收的最重要开源项目之一。
那会大家只知道,Google 的编译器房间里,诞生了一个不安分的孩子——它不是来替代谁的,它是来让所有人少造点屎山的。
二、MLIR:不只是又一个中间表示
在编译器里,中间表示(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)就像老小区楼里的下水管道:平时谁都不想动,一堵了,全楼都遭殃。
LLVM 的 IR,已经陪伴业界二十年。它稳、泛用、优化能力强,几乎成了编译界的“标准答案”。但也正因为如此,它显得太“硬”,太“统一”,也太不适合多样化的 AI 世界。
Chris Lattner 很清楚这一点。他自己就是 LLVM 的亲爹,哪怕别人不敢吐槽,他敢。他知道 LLVM IR 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性能,而在于它没法优雅地表达 AI 的复杂性和层级感。
现代 AI 模型是分层的:高层是前端语言(Python、TorchScript)、中间是各种算子图(Graph IR)、底层是张量调度(Scheduling IR)和硬件调用(Codegen IR)。你不能用一套固定格式从头吃到尾,那就像拿个锤子修手机一样,除了砸碎,啥也干不了。
所以 MLIR 做了一个看似冒险、实则革命性的设计:“放弃统一格式,拥抱方言(Dialect)。”
✦ Dialect:不是妥协,是策略
MLIR 的核心概念,就是允许不同的子系统、不同的抽象层级,各自定义自己的语法、语义、算子集和优化规则。
你可以把一个 Dialect 理解为“一套规则自洽的小语言”,专门描述某一类操作,比如:
-
linalg dialect:负责线性代数张量调度。
-
tensor dialect:负责形状、类型推理和广播语义。
-
arith dialect:基础算数运算,统一数值类型。
-
tosa / mhlo:分别是 Android 和 XLA 系统自带的算子 IR。
-
自定义 dialect:你可以为你的 ASIC/NPU 写一套专属 dialect,跑得飞快谁也拦不住。
更重要的是,这些 dialect 不孤立,它们都可以“降级”到下一级,更底层的 dialect,最后再转换为 LLVM IR 或者直接代码生成。
这种设计的好处,是把编译器这个“大一统”的黑箱,拆成了一层层可以插拔、可组合的“模块”。你想自己重写某个环节,不用 fork 全套源码,也不用跟别人对齐优化策略,你只要造个 dialect 就行。
✦ 组合不是卖点,是生存方式
AI 框架碎片化、硬件百花齐放,其实是行业的常态,而不是意外。与其指望全世界统一规范,不如设计一套系统——允许大家“带着差异合作”。
Chris 在 MLIR 的设计文档里说过一句话:
““传统编译器是为稳定的硬件和语言设计的。但 AI 是不稳定的,永远有下一个模型、下一个芯片、下一个优化方向。” “所以 MLIR 的目标不是统一所有,而是支持多样性的秩序演化。”
这种“反统一”的统一,其实才是真正的工程理性。与其天天重造轮子,不如把轮子做成标准接口,谁家都能插进来跑几圈。
✦ 不是工具,是平台
MLIR 被称为 “a compiler framework for building compilers” 不是开玩笑。它不是为谁而生的,而是为所有人准备了一个抽象平台。
你可以用它做:
-
AI 编译器(OpenXLA、Triton、Shark)
-
图形处理 DSL(RenderScript 的替代品)
-
硬件描述语言(CIRCT、FIRRTL)
-
量子计算编译(QIR)
-
自定义 DSL 的快速原型(像 Swift for TensorFlow 当年)
甚至,有人用它写了 FPGA 的逻辑合成工具链。
MLIR 没有说自己是“AI 专用 IR”,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被锁定成“框架附庸”或者“语言附庸”。它做的是底座,是底层的“共识操作系统”。
✦ 技术理想的第一步,必须架构正确
技术界常说:“架构是你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。” 如果你一开始选错了抽象,就会在三年后写出一堆无法 refactor 的代码山。
Chris 和 MLIR 团队正是痛过 LLVM 的“硬统一”,也经历了 AI 编译器的一地鸡毛,所以他们赌了一把:与其为了性能牺牲结构,不如为了结构暂时牺牲性能。
这个赌注,在后来 OpenXLA 和 Triton 的演进中被证明是值得的。但真正的麻烦,也才刚刚开始。
下一节,我们要讲讲 MLIR 是怎么从一个技术理想,变成 Google 各大团队争相使用的“基础设施”,以及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“技术太成功、合作却越来越难”的悖论。
三、Google 式温床:从 TPU 到 TensorFlow Lite 的全面内化
MLIR 诞生之初,就不是给“用户”准备的——它更像是 Google 给自己解内伤的一帖药。
Chris Lattner 和团队做出的这个工具链底座,第一批用家根本不是框架工程师,而是那些天天在跟硬件编译痛苦搏斗的 Google 内部开发团队。尤其是几个——TPU backend 团队、TensorFlow Lite 团队、XLA 工程组,还有一堆为 Pixel 手机写 NN API 的前线工程师。
为什么他们急着上 MLIR?一句话总结就是:
““我们不想再写第二套 XLA。”
✦ XLA:不得不维护的“定制版编译器山寨王国”
XLA(Accelerated Linear Algebra)是 TensorFlow 为了支持高性能加速器(TPU、GPU、CPU)搞出来的一套子编译器系统。起初定位是优化矩阵乘法,后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型编译器框架,能干常见的 kernel fusion、layout 优化、buffer 重排等等。
听起来不错吧?问题在于:XLA 是为了 TensorFlow 的抽象层定制的,换个框架它就懵了;换个芯片它就卡了。
而且,它不 modular,Pass 链之间依赖巨多,优化策略又深度耦合前端语义。你想自己加一个硬件 Target 或者特殊 Op,得 fork 半个 XLA,手动灌入行为——搞到最后,一堆团队各自养了一套“魔改 XLA”。
这就是 Google 内部的“编译器塔楼”。每一个 TP 编译器工程师都在上面贴瓷砖、补水泥,哪一层塌了都能砸死人。
✦ MLIR 进场:不是替代 XLA,而是结构重构
MLIR 不是一刀切地“替换” XLA,而是作为一个更底层、更灵活、更抽象的通用框架,被一点点“塞进” XLA 和 TensorFlow 现有系统里。
最先开始的,是 TensorFlow Lite 的转换链。
TFLite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要从 TensorFlow Graph 转成优化过的 flatbuffer 模型,过程极为脆弱。量化流程、fuse pass、op lowering 全靠拼硬编码。
MLIR 则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优势:你可以用 Dialect 方式精细建模模型中每一个计算步骤的“意图”(intent),再通过多个层级的 IR(比如 from TensorFlow Dialect → TOSA Dialect → Linalg → LLVM IR)来逐步转换优化,而不是一次性硬推。
于是,TensorFlow Lite 成为了 MLIR 的第一块“大规模落地”试验田。
接着是 TPU 编译器团队。他们当时正被一堆自定义指令和 on-device scheduling 烦得焦头烂额,用传统 IR 根本表达不了“硬件亲和性”的复杂调度需求。
MLIR 则允许他们直接造一个 TPU Dialect,写明特定算子和指令绑定,调度策略也可以 modular 插入。他们第一次觉得,写编译器不是一场负担,而是可以“搭积木”做定制的事情。
Chris 后来曾在一次内部 Tech Talk 上说:
““我们不是来告诉你怎么做编译器的,我们是来给你一堆构建编译器的工具。你要造城堡、修下水道、挖矿井都行,只要结构清楚,别人就能接得上。”
这话一下打通了 Google 内部很多编译器工程师的心结。尤其是那些为定制芯片写 Lowering Pass 的老工程师,他们第一次有了“用规范方式写屎山”的手段——结构感回来了,维护成本也能控了。
✦ 内化爆发:从研究工具到 Google Infra
MLIR 真正的爆发,不是某个产品线接入,而是变成了“Google Infra”里默认可调用的一部分。
-
TensorFlow 全线开始接入 MLIR 架构,用作 TF Graph 到 XLA IR 的桥梁。
-
TFLite 直接切到了 MLIR Pipelines 上。
-
Android 团队用 MLIR 写 NNAPI 编译 Pass,提升了模型加载兼容性。
-
Research 团队用 MLIR 做 JAX 实验性后端,还探索了 LLVM 后端的混合优化。
甚至连 Google Cloud Infra 也在某些加速服务中引用 MLIR 构建优化路径。
Google 没有正式宣布 MLIR 成为“统一编译工具链”,但工程师们知道——MLIR 是唯一一套“大家都能用、还能互相复用”的编译器组件。
这时候,Chris 和他的核心团队意识到:如果这套架构只停留在 Google 内部,那它终将还是成为另一个“巨头内部黑箱”。
他们决定把它捐出去,开源,并推动走向 LLVM 社区。
一场真正意义上的“工业级开源协作试验”,就此开始。
但他们没想到,技术的成功只是第一阶段,接下来的,是协作的地狱。
四、理想主义爆发:开源捐赠与行业狂欢
对于很多工程师来说,编译器只是工具,不是信仰。但对 Chris Lattner 来说,编译器是一种秩序,是用来统合混乱、缩短试错周期、避免重复发明的基础设施。
他做过 LLVM,知道“好架构”得有个“公共的家”——否则它只会在巨头公司内部自生自灭,被流程、KPI、遗留代码一点点吞掉。
所以,在 MLIR 被 Google 内部多个大项目接纳之后,Chris 做了一个大胆又纯粹的决定:把 MLIR 开源,捐赠给 LLVM 基金会。
不是挂在 Google GitHub 下面,不是 Apache 项目,也不是 TensorFlow 附属模块,而是——正式成为 LLVM 社区的一员。
这一步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 MLIR 不是“服务 TensorFlow 的编译模块”,而是被赋予了独立生命,是可以服务整个行业的中立技术基础设施。
“Chris 原话是:“If MLIR has a chance to unify the world, it must be free from any single company’s control.” ——“如果 MLIR 真能统一世界,它必须脱离任何一家公司控制。”
✦ LLVM 社区:技术人最后的庇护所?
LLVM 社区跟多数开源项目不同。它老、严、偏工程,不讲互联网“社区管理套话”,也不搞“基金会背书 PR 战”。它讲的是 meritocracy——谁写得好,谁就能说话。
MLIR 挂靠进 LLVM,最直接的好处是:工程上继承了 LLVM 的测试、基础组件、工具链环境;文化上继承了“开放协作、拒绝私货”的基本规则。
Chris 和核心团队也组织了开放的 “MLIR design meetings”,每周一次,不管你是 Google、Apple、Intel、初创公司,甚至独立黑客,只要你愿意做贡献,就能来参与设计讨论。
这在工业级编译器项目里,几乎是第一次。
✦ 开源第一波浪潮:一窝蜂的方言热潮
开源后半年,MLIR 社区进入“疯长阶段”。
各家公司纷纷 fork、改、扩展:
-
Intel 搞了 OneAPI 后端和 VPU Dialect。
-
AMD/Xilinx 造了 FPGA 专用 Dialect,用来描述时序电路行为。
-
NVIDIA 开始内部评估 MLIR 用于 Triton 编译链替换。
-
Meta 内部某 PyTorch 工程组也开始玩 MLIR 作为 IR Fusion 引擎。
-
一堆初创公司(包括后来 Modular 和 Cerebras 的前员工)都开始基于 MLIR 开发定制化 compiler stack。
那时候 MLIR 社区 Slack 一天 500 条消息,Pull Request 排队能排到下周,Design Review 文档成了最常刷的“开源剧本”。
每家公司都说:“我们不是重造轮子,我们只是造我们那一块。”
——听起来都很合理。但大家加起来,其实又开始了新一轮“轮子内卷”。
✦ 没有核心领导的开源,是种集体幻觉
Chris 当时还在 Google,不能长期做 MLIR 的“社区领袖”。LLVM 基金会也一贯不干预技术细节,只管法律和治理框架。
于是,MLIR 社区变成了一个“技术强者自治、目标随缘决定”的生态。也就是说:谁写得多、写得快,就能定方向。
这看起来民主,实则脆弱。
-
有人为了兼容 TensorFlow,写了很多 ML-specific Dialect。
-
有人搞硬件后端优化,写了一堆 Lowering Pass。
-
有人为了教育目的,用 MLIR 改造成教学用 compiler demo。
每一段代码都很有道理,但堆在一起就是一座迷宫。没有一条“主线”,没有一个“统一落地的 reference stack”。
Chris 后来回忆,那段时间就像回到了 LLVM 刚开源那几年:
““Everyone had a slightly different vision of what MLIR should be.” ——“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MLIR 梦。”
可梦多了,就容易碎。
✦ 从理想到混乱,只隔着一个“方言爆炸”
最开始 Dialect 是为了 modularity,为了复用。但当每个团队都写自己的 Dialect、加自己的 Type System、搞自己的 Pattern Matching,整个 MLIR 仓库就变成了一座“语法公园”。
而真正想“从模型直接跑到硬件”的开发者——傻眼了。
-
没有一套明确的 Reference Dialect Set。
-
没有官方推荐的 Pass Pipelines。
-
没有标准的 Graph → Lower → Codegen 路线图。
-
每家公司都说“我们自己写了一个 MLIR stack”,但都互不兼容。
就像当年的 OpenCL:都说自己开源、开放、中立,结果每家公司都偷偷加了扩展,最后没有人敢用“原生 OpenCL”。
Chris 那段时间做了一件挺感慨的事:
他提议把所有 AI 相关的 Dialect,从 MLIR 主树中 逻辑“拆分出去”,成立独立 area group,并建议重命名,例如叫做 “TensorIR” 或 “MLIR-AI”,以免混淆“MLIR Core”的纯粹性。
这是一次晚来的治理尝试——但已经有点晚了。
因为此时,所有人都在用 MLIR,却没有人能控制 MLIR 往哪里走。
五、分裂,从内部开始
一个技术项目的终点,往往不是“被放弃”,而是“被太多人使用”。
MLIR 就是这样一个项目:它没被冷落,恰恰是因为太受欢迎,最终被拉扯成了一张巨网,每个方向都有力量,但没有一个方向能带动整体。
而一切分裂的起点,来自一个看似积极的变化:
“Google 的 MLIR 原班开发者,陆续离职了。
插播宣传一下,MLIR书即将出版(2025年5月15日前出版,清华大学出版社),《MLIR编译器原理与实践》,打扰您了!或知乎链接: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8989590488015094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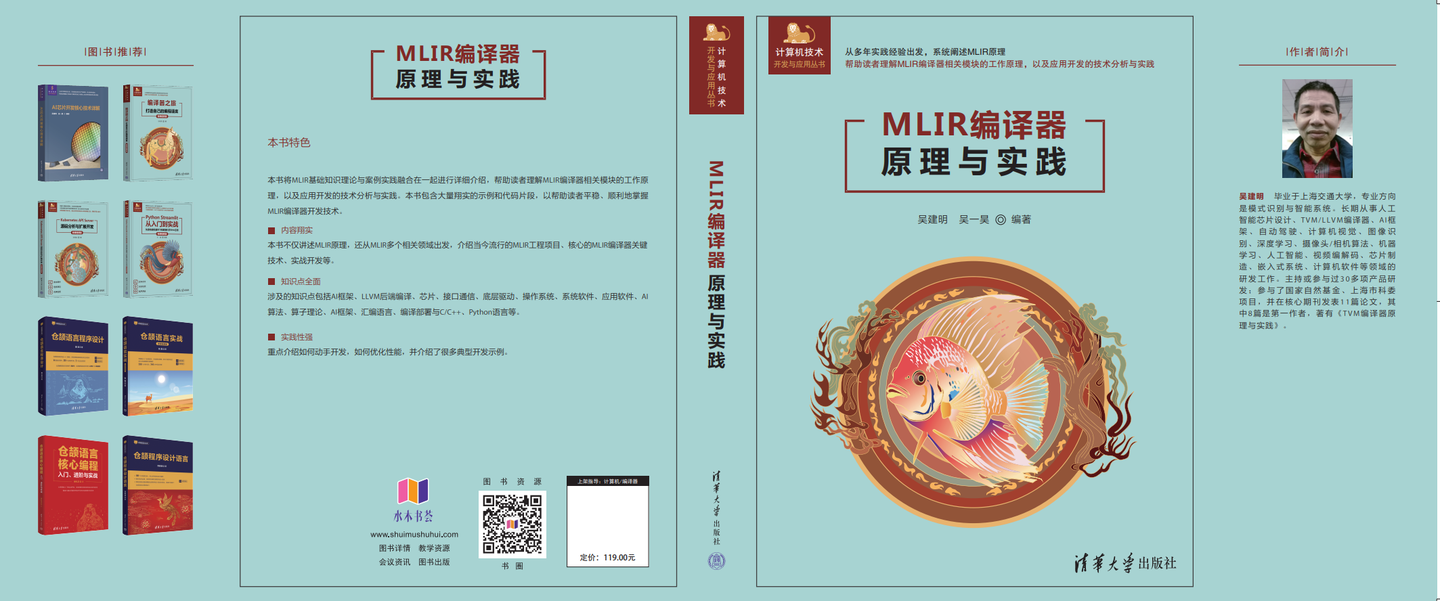
✦ 为什么其他硬件公司做不出 CUDA?
这个问题,已经被问过无数次。答案其实残酷又简单:
“CUDA 不只是软件,它是一个商业战略,是一个 技术闭环 + 应用闭环 + 客户成功闭环 的集合体。
而其他公司——无论是芯片厂、框架厂、系统厂、创业公司,都只在某一个环节努力,缺乏全局统一力。
再加上行业内的现状是:
-
工程师能写 compiler,但没人能管芯片线;
-
硬件团队懂 kernel,但不懂 PyTorch 生态;
-
软件团队想优化模型,但拿不到底层 Spec;
-
商业部门想卖方案,但没人愿意给客户修 bug。
于是,就算大家都用了 MLIR,最终做出来的也只是一个个“半残 compiler”,没一个能跟 CUDA 打正面硬仗。
Chris 在一次访谈里苦笑说:
““MLIR 成功地让每家公司都可以写一个编译器,但也让每家公司都在重复造 compiler,而没人写出能对抗 CUDA 的产品。” ——“A thousand compilers bloom, but none beat the king.”
✦ 所以 MLIR 是失败了吗?
这就像问“Linux 是不是失败了”,显然不是。
MLIR 成功地重塑了现代 compiler 的底层结构,是无数新 compiler 项目的技术基座,它让业界告别了“每家公司从 LLVM 开始写 Pass”的时代。
但它不是产品,不是解决方案,也不是行业生态整合器。它是一把锤子,不是一座房子。
而 CUDA,是早就盖好的别墅,你只需要搬进去——即使房型不能改、租金死贵。
对开发者来说,选择往往不是技术多好,而是谁的房子能先住。
七、新希望?MLIR 社区的治理重构尝试
在编译器世界,失败通常不是因为代码写得烂,而是因为方向失控、治理缺位、共识丧失。
MLIR 没有失败,但它离“共识破裂”只差一步。
Chris Lattner 离开 Google 之后,MLIR 社区进入了“无明确领袖、全靠工程惯性推进”的阶段。Pull request 依然源源不断,Dialect 依然百花齐放,但所有人都在问——我们到底在往哪走?
就在这种摇摇欲坠的时刻,LLVM 社区出手了。
✦ Area Governance:LLVM 老派治理哲学重启
LLVM 是老牌社区,治理方式不 fancy,但很稳。
不像 CNCF 或 Apache 基金会搞 Steering Committee、Technical Oversight Board 那一套,LLVM 的哲学很朴素:
“谁写得多,谁说了算。但写得多的人,必须对社区负责。
于是,在 2023 年,LLVM 为 MLIR 成立了一个新的治理框架:
-
拆分出两个主要子领域(Areas):
-
MLIR Core:专注基础 IR 结构、类型系统、Pass 管理、工具链;
-
MLIR Dialects:负责各种领域特定的子 IR,尤其是 AI 编译相关的 linalg、tensor、arith 等。
-
每个 Area 组建 “Area Group”,设立 Maintainers(可类比核心 Committer);
-
推出《MLIR Charter》文件,定义每个 Area 的目标、范围、变更流程和协作接口;
-
开放 Design Call,鼓励社区成员提交新 Dialect 规范、Pass 管线演进建议;
-
设置长期计划(RFC),以“愿景文档”的形式推进跨公司协作共识。
这一系列动作,看起来很“开源治理味儿”,但对于长期处于“自由生长、缺乏主线”的 MLIR 社区来说,这是一次集体重塑方向的尝试。
Chris 后来在一次社区公开信中写到:
““我希望大家不要把 MLIR 看成一个 compiler project,而是看成一个 platform project。平台的治理,不是靠谁聪明,而是靠大家愿意‘对齐’。” ——“Platform projects succeed when the community converges on constraints.”
✦ 技术对齐之外,命名也是治理
除了结构治理,社区还尝试解决一个长期以来的“语言污染问题”:
““MLIR”到底是指 core IR,还是指整个 AI 编译栈?
这个问题已经造成了广泛混乱——比如有开发者以为 MLIR 是 XLA 的别名,有公司内部把 “我们的 ML compiler” 简称叫 MLIR,实际是个魔改版本。
于是,有人提出:是不是该给“AI 编译相关的 Dialects”换个名字?比如叫 TensorIR 或 MLIR-AI?
这事没有最后定论,但在社区里被认真讨论。它代表了一种态度:
“与其混着用、不清不楚,不如割开来,保核心,放创新。
这种“命名治理”,看起来小事,实际是基础设施系统中最难的一环:定义边界。
你不定义清楚边界,合作的前提就不存在,规范就落不了地,生态也永远搭不起来。
✦ 开源社区的集体坚韧
更重要的是,MLIR 社区并没有像很多“红火一时”的项目那样,在关键节点散掉。相反,它的工程师群体仍在坚持维护和演进。
-
Google 仍在投入人力,维护 OpenXLA 和 Core Dialects;
-
Apple 开始用 MLIR 构建 Swift 编译链的一部分;
-
一些高校和研究组参与优化调度、多目标硬件映射研究;
-
LLVM 社区的编译器老兵,依然每周在 MLIR Call 上点评 PR、修 bug。
你甚至可以说:MLIR 是在无商业公司主导的情况下,靠工程师集体意志撑下来的。
它没有老板,没有产品经理,没有“必须发布的 deadline”,但它活着,而且每个月都在进步。
✦ 但治理能修复生态吗?
这一点,哪怕是 Chris 自己,也说得很清楚:
““治理能防止恶化,但不能自动创造统一。” ——“Governance curbs entropy. It doesn’t create coherence.”
AI 编译器生态的问题,不只是 MLIR 的问题,而是整个行业共同的问题:
-
没有跨公司协作的强动力;
-
没有商业共赢的机制约束;
-
没有大厂愿意主导 reference stack;
-
更没有开发者认同“共建生态”的心智成本。
MLIR 的治理重构,可能让它重新稳住了“底层基建”的身份,但它能不能再往上搭建出统一的 AI 编译栈?还是个大大的问号。
Chris 曾说,如果时间能倒流,他希望当年把 AI Dialect 独立出来,给它取个新名字,单独治理。那样也许就不会让 MLIR 这么快“身份混乱”。
但时间不会倒流。技术治理,注定是在废墟上建秩序,在混乱中找平衡。
八、结语:美好设计不是梦,只是太早了
MLIR 从不是一个失败的项目。它甚至可以说,是现代编译器世界里最成功的技术创新之一。
但它也不是一个成功的“解决方案”。
它像一艘远航船,被极少数人提前造好、提前放入水中,企图带着整个产业穿越碎片化的编译海洋。但当它刚出港,甲板上就上来了太多公司、太多期望、太多不同方向的舵手——结果,它没有沉,却也没法走远。
从 2018 年那场白板会议开始,Chris Lattner 想要解决的,不是某个模型的性能瓶颈,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:
“AI 软件栈的复杂度,已经超过了人类组织架构的治理能力。
我们造了太多工具,但缺少底层统一逻辑; 我们推动了太多硬件,但每一个都想当生态主角; 我们开源了大量代码,但彼此之间互不理会、各走各的。
MLIR 的设计,试图以一种结构主义方式重新组织混乱世界:通过 Dialect、IR 层级、模块化,让每一个“局部理性”汇聚成“全局秩序”。
从技术上说,它做到了——LLVM 做不到的动态扩展性、TVM 做不到的多前端后端组合、XLA 做不到的解耦性,它都做到了。
但从产业上说,它也失败了——没能统一生态、没能凝聚共识、没能阻止新一轮的“AI 编译器割据战”。
Chris 在一次 MLIR 社区 AMA 里被问到:“如果能回到2018年,你还会选择做 MLIR 吗?”
他笑了笑,说:
““会。因为不做,就没人做了。” “但我会做得更小、更慢、更闭源,先把一整套 reference stack 打通,再开源。” “我太相信工程师的自律了,却忘了商业的焦虑和组织的本能。” ——“I overestimated developer discipline and underestimated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.”
这其实是一切底层系统工程的通病。
我们都希望用架构解决问题,但架构不能替代治理; 我们都希望共建生态,但生态不能自发协调; 我们都希望“开源 + 产业协作”能打赢“封闭 + 垂直整合”,但现实往往反过来。
CUDA 成了事实标准,不是因为它技术多先进,而是它从头到尾有人兜底,有人主导,有人为性能结果负责。而 MLIR,只是一群技术人写给技术人的礼物——它干净、强大、优雅,但却太依赖使用者的理解和构建能力。
它不是错了,只是太早了。
也许十年后,当 AI 编译器终于不再是“每家公司都得养一队”的苦活累活时,MLIR 会像 LLVM 一样,悄无声息地站在底层,支撑起所有理所当然的“自动优化”。
那时候,我们才会真正理解:这不是一个失败的统一梦,而是一场延迟兑现的技术遗产。
最后,宣传一下,MLIR书即将出版(2025年5月15日前出版,清华大学出版社),《MLIR编译器原理与实践》,打扰您了!或知乎链接: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8989590488015094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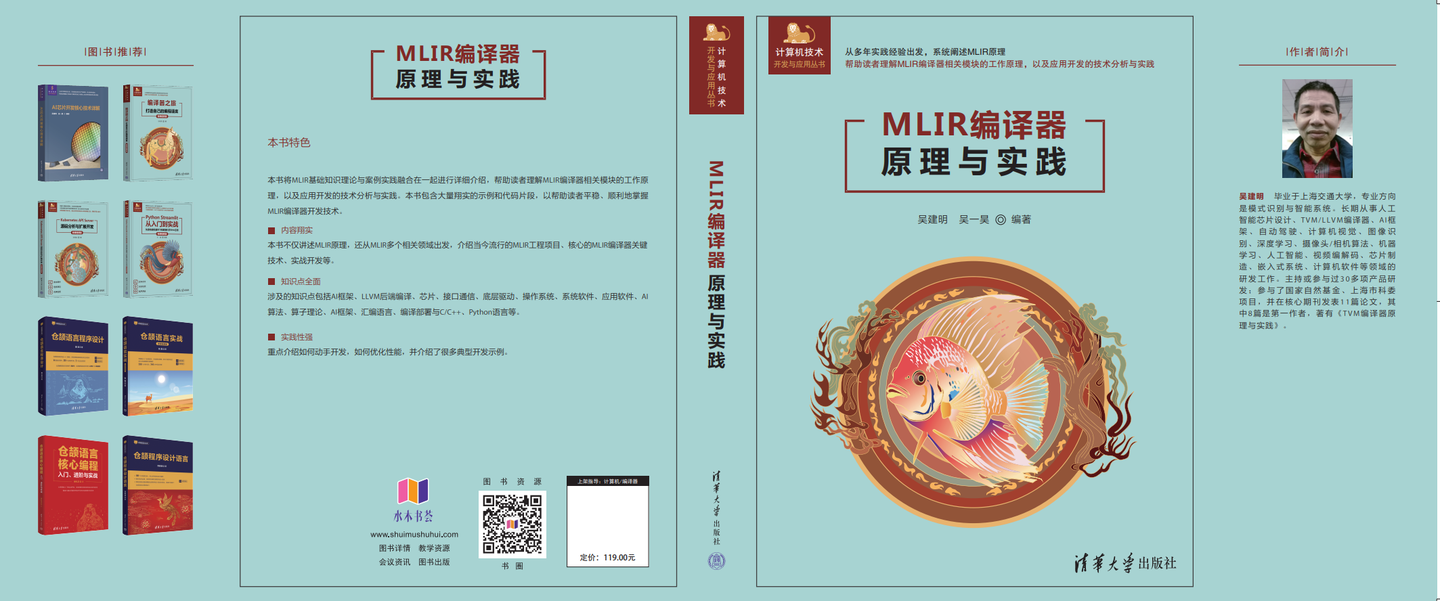
添加图片注释,不超过 140 字(可选)
参考文献链接
人工智能芯片与自动驾驶



 浙公网安备 33010602011771号
浙公网安备 33010602011771号